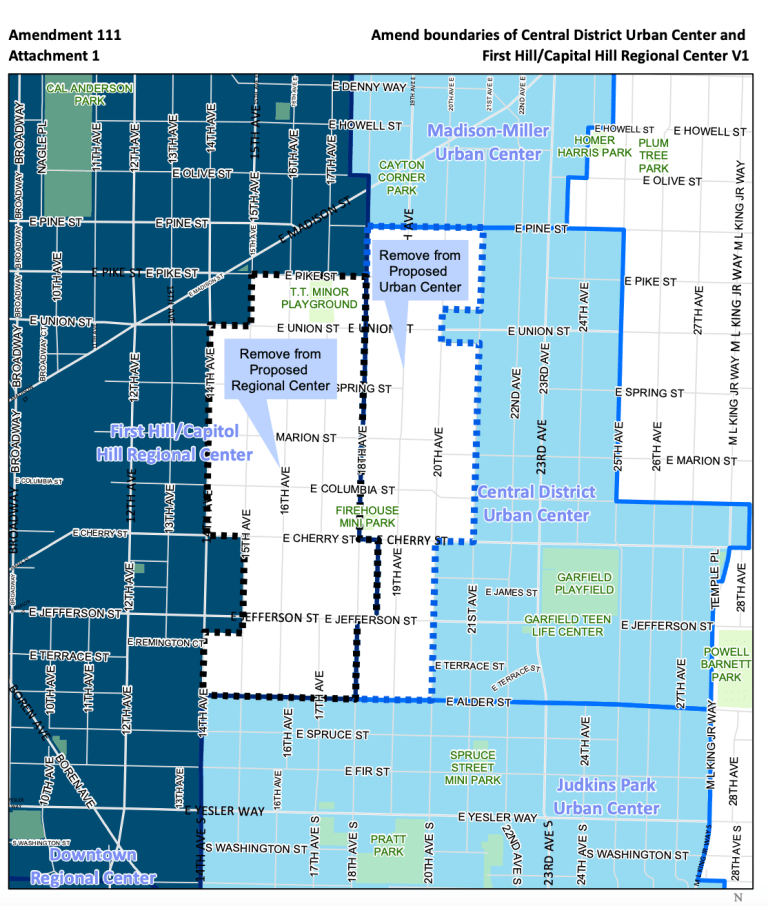图片源于:https://www.thestranger.com/guest-editorial/2024/12/09/79817227/tammy-moraless-resignation-exposes-a-pattern-of-institutional-abuse-against-southeast-seattle-electeds
西雅图市议员塔米·莫拉莱斯上周三宣布辞职,东南西雅图不仅失去了这位长期的、历经考验的代表——我们再次因有勇气选举一位为我们社区利益而激烈斗争的领导人而受到惩罚。
作为东南西雅图的居民和工人,我们共同经历着历史上被压迫、被划红线和投资不足的工薪阶层社区所带来的代际创伤和日常现实。
这些斗争塑造了我们的政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两次选举塔米·莫拉莱斯来倡导我们社区急需的进步政策和投资。
在第2区集中有如此多的黑人和拉美裔社区时,莫拉莱斯深刻理解了以种族公平为中心、优先考虑真实的社区参与、修复对我们社区造成的伤害的必要性。
我们深知领导层在我们地区失败的历史和模式——反过来,这也反映了制度对我们所选择代表的领导者的失败。
当我们阅读莫拉莱斯在我们的区发布的声明,描述一个充满管理不善、骚扰和恐吓的文化时,我们感到愤怒但并不惊讶。
尽管她的议会同事对信任和共同治理的侵蚀令人极为担忧,但我们尤其愤怒的是她在同事们手中遭受的待遇。
让我们明确:莫拉莱斯并不是在抛弃她的选民。
像任何面对敌对工作环境的人一样,她选择远离一个让她受到强烈骚扰并妨碍她有效服务我们区的职务。
我们区的愤怒并不应该指向莫拉莱斯选择退出一个敌对环境,而是应该指向导致这种敌意的机构。
我们认识到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她的同事有意将一位代表城市唯一少数民族多数区的有色女性排挤出局。
她的辞职不仅反映了同事们在共同治理方面的失败,而且是对抗制度性种族主义更广泛模式的一部分,这种模式延续了对努力提升我们社区需求和声音的黑人和拉美裔领导者的伤害。
一个两者并存的立法机构
莫拉莱斯在议会上的待遇突显出一种有毒文化,这种文化曾经将前37区州代表基尔斯滕·哈里斯-塔利推向了州立法机构的边缘。
这种文化以集权控制、压制异议和缺乏诚信为特征,优先考虑无效的权力动态,而非有意义的变化和民主进程。
作为选举这些领导者的选民,我们看到了当前议会成员的经历与我们前州代表的经历之间明显的相似之处。在《南西雅图翡翠报》发表的一封信中,哈里斯-塔利描述了她被边缘化的经历:“当你提出一个不受欢迎的问题时,它会被忽视或忽略。当你利用你拥有的工具时,你会被提醒‘我们在这里不这样做’。当你对领导层提出异议或表达不同意见时,你会被沉默或羞辱以让你排队。”
当议会成员,包括马里萨·里韦拉,批评莫拉莱斯因前者尝试冻结高度受欢迎的经济发展倡议(EDI)的资金而发送行动提醒时,我们亲历了这些联系。
另一个例子是,当莫拉莱斯在她的同事面前捍卫EDI立法时,她与同事们发生分歧,这项立法为多家服务于东南西雅图的组织提供资金。
其他形式的伤害亦延伸至市议会的最高权威。
哈里斯-塔利在指责不受欢迎的问题被忽视,甚至受到惩罚时,让我们想起了市议会主席萨拉·纳尔逊如何在莫拉莱斯因提起有关推迟决定是否将I-137(创建可持续的社会住房开发商收入来源的公投倡议)置于议程的合法性问题时关闭了她的发言机会。
即使在国家立法机构的敌对环境中,哈里斯-塔利依然在她的同事和参议员中找到了盟友和朋友,他们愿意合作并朝着共同目标努力。
然而,这种支持并没有传递给莫拉莱斯,后者发现自己被孤立在一个保守的议会多数之中。
正如埃里卡·巴奈特在接受《Publicola》采访时所说:“她感到惊讶的是,她的同事中有很少有人表现出与她合作的兴趣。”
通过拒绝与我们的议员合作,议会明确表示他们同样拒绝倾听第2区的声音。
从市到县
我们目睹的对莫拉莱斯的敌对行为是由于一种文化所驱动,该文化允许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施加伤害。
这个议会将自己呈现为一个关注效率和生产力的务实立法机构,尽管这可能会以牺牲诚信为代价。
当掌权者进行有害行为时,敌意进一步得以助长,比如当市议会主席纳尔逊故意跳过一个委员会会议以为莫拉莱斯的对手竞选,直接对我们的议员发起攻击,而非为城市服务。
外部人员感到有权直接攻击我们的领导者,以便在他们无法为自己辩护或解决伤害时,这种模式并非仅存在于莫拉莱斯与主席纳尔逊之间的动态中。
它回响着另一位代表东南西雅图的议会成员——吉尔梅·扎海莱——的经历,他曾遭到其前同事凯西·兰伯特通过她的选区发出的种族邮件的攻击。
然而,在县级,后果迅速。
兰伯特被剥夺了所有委员会任命,显著减少了她在议会的角色。
社区成员呼吁她辞职。
虽然她失去了连任竞选,但我们区的声音迅速指出县议会的行动未能实现恢复信任所需的问责。
我们的县领导决不能容忍这种赤裸裸的虐待——我们的城市同样如此。
如果有人想了解主席纳尔逊如何处理这种丑闻,我们可以指出她如何授权、使能并积极参与对莫拉莱斯的公开敌对。
即使是半措施的正义似乎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公然的事实
我们区清楚,其他议会成员直接共谋维持对我们地区领导者实施这种制度性虐待的模式——他们甚至没有试图掩饰。
正如巴奈特所写:“恶名常常是公开和明显的。”
而不是将莫拉莱斯视为同事、市议会最高资深议员和代表超过十万居民的人,这个议会反复选择将她去人性化,单纯将她作为前议会的象征。
当议会新成员如罗伯特·凯特尔在莫拉莱斯在场时把所有机会用来批评前议会时,明显表现出这一点,集体无视她的前任,无尊重或承认。
作为代际和当前的创伤受害者,我们理解,当有人呼喊虐待时,第一步是倾听而无评判。
我们意识到不存在一个“完美的”受害者,每一个人际情境都蕴含细微之处。
然而,议会成员罗布·萨卡在回应莫拉莱斯辞职信时的评论令我们特别愤怒。
萨卡将我们议员对她遭遇的严重关切和议会权力制衡侵蚀的问题轻描淡写为“尖锐的修辞和分裂政治”。
萨卡的话 stark成为虐待受害者在提出关切时常常遭到无视或被淡化为拥护者的生动提醒。
无论是单独一个人还是一整社区的人,揭露施加伤害的方式均无完美:他们更愿意选择沉默。
作为议会领导者,市议会主席纳尔逊有直接的责任与议会同事之间修复人际伤害。
这一责任已经被议会主席轻松抛弃,就像她的政策立场与选民的利益明显对立,纳尔逊作为立法部门领导者的官方行为也是挑衅和不代表该民主的。
纳尔逊曾切断评论,并监督逮捕发声的社区成员,质疑选民的智商,且不必要地解雇了在进步和保守议会工作过的中央工作人员领导。
在莫拉莱斯对我们区提到的信任危机问题上——这是我们作为她的选民强烈肯定的一个危险趋势。
鉴于纳尔逊和其他议会成员所营造的敌对环境,毫无疑问,莫拉莱斯所经历的虐待、孤立和排斥可能影响到其他议会成员或市政府工作人员的投票、行为或决策。
放在纳尔逊桌上的辞职信不是她领导下的孤立失败——而是反映了她治理在城市政治中的核心主题:对任何持不同政见者的恐吓、排斥和骚扰。
那么,接下来会怎样?谁将是下一个?
下一位代表东南西雅图的议员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显然,议会多数对于通通过进步政策缺乏兴趣,这些政策将给我们的区带来投资。
我们无法承担另一个只会跟随多数的、简单地压制那些远离正义的西雅图人声音的无效议员。
值得失去的一位榜样是新当选的议员亚历克西斯·梅尔塞德斯·林克,她代表我们的社区担任市级议员。
在她上周二的就职演说中,她承诺将她的市级席位打造为“人民办公室”。
超越修辞,她承诺与所有议会成员合作,追求进步性收入流来应对预算赤字,寻求危机响应的非暴力替代方案,并捍卫西雅图免受可能的第二个特朗普总统任期的影响。
这些都是体现莫拉莱斯在议会工作中所展现出的领导品质和政策立场。
多亏了林克,我们区超过十万居民可以放心,我们不会完全没有代表。
在撰写这篇集体回应时,我们承认一个不幸的现实:如果我们的长期代表在议会多数面前争取合作遇到困难,那么我们所期待的继任者很可能也面临类似的挑战。
一位勇于面对挑战的第二区邻居将需要接受,成功不仅是在立法上获得通过——而是在坚定我们的价值观和目标中取得成功。
我们新当选的议员必须对一个赋能东南西雅图的黑人和拉美裔工薪家庭的运动负责,并且还必须超越问责,积极成长并利用一个大众运动。
如果我们希望看到工薪家庭的利益在2027年重夺议会多数,我们需要能够激励和动员第二区工人的领导者。
任何形式的正义只能通过对议会运作方式的全面变革实现——不仅作为一个立法机构,还是作为一个人群的集合。
那些共谋创造导致我们议员辞职的敌对环境的领导者,绝非欢迎我们下一个当选议员的领导者。
该议会需要进行全面的自我反思,只有在这之后他们才能重新回归到最能解决共同治理关系缺失的最佳成立状态。
作为第二区的居民,我们的声音代表着一个庞大、多样化、多元种族、跨民族和跨代际的社区——这些身份在历史上以及继续被边缘化,且在即将到来的总统任期下可能面临更大的挑战。
当我们的民选领导者遭到无情的反对和根植于制度性虐待的骚扰时,我们的区如何维护对民主过程的信任?
这个问题只能由那些身处制度权力位置的人来回答。
但无论谁在政府中代表我们,作为邻居,继续组织以保持自身安全是我们的责任。
和与我们共同撰写这篇社论的第二区选民一起,以下社区组织也联合签署了支持声明:华盛顿巴士,华盛顿社区行动网络,谁的街道?我们的街道!,西雅图学生联盟。
贝利·梅迪洛是华盛顿巴士的数字与传播组织者,也是南西雅图阿纳克巴扬的成员。
安·阮是华盛顿大学的学生,居住在雷尼尔海滩。
奥利弗·米斯卡是华盛顿民族研究现状的政策主管,居住在哥伦比亚城。
玛丽亚·阿班多是街道与社会组织者,居住在国际区。
KL·香农是西雅图马丁·路德·金组织联盟的副主席,也是街道与社会组织者,居住在Othello。
韦斯·斯图尔特是一名社区组织者,居住在哥伦比亚城。
艾玛·卡塔基是性别暴力组织者,前西雅图社区警察委员会联席主席,也是API Chaya的创始人,居住在哥伦比亚城。
克拉拉·坎托是街道与社会组织者,居住在雷尼尔谷。
艾米贾·史密斯是一名社区组织者,居住在东南西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