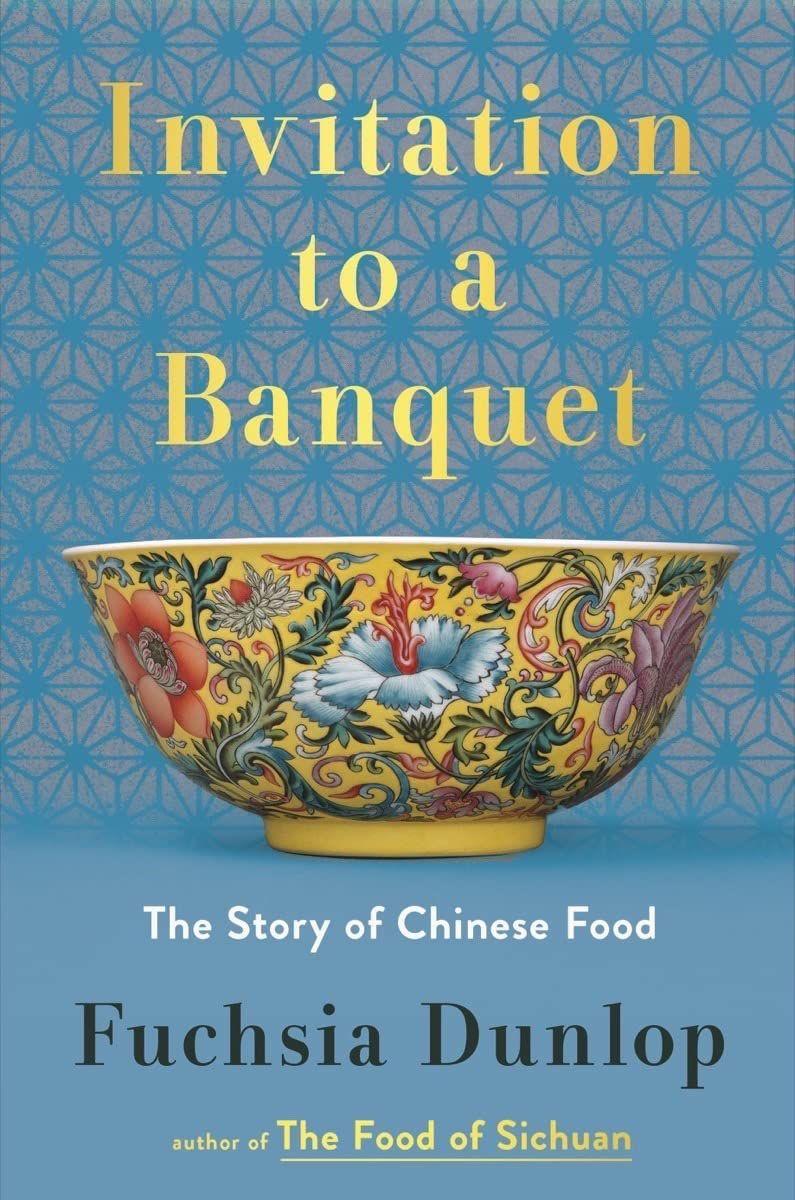图片源于: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explaining-chinese-food%E2%80%94and-china
在20世纪初,中国改革者对祖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弱小感到失望,强调需要通过放弃传统的儒家思想,采用西方的民主和科技等观念来实现现代化。
一些人受到19世纪末日本现代化知识分子的启发,甚至在个人生活中采纳西方的饮食习惯,如饮用冰水和吃牛肉。
尽管当时中国社会存在强烈的反叛主义,但对于“饮食现代化”的推动依然引发了巨大的抵抗,革命领袖孙中山对此尤其反对。
他认为,尽管传统中国文化存在明显的不足,但中国的饮食传统却是一个例外,展现了中国文明的巨大潜力。
他曾写道:“中国在所有现代文明领域落后于其他国家,唯有饮食,从未被任何文明国家超越。”
对于一个软实力匮乏的国家来说,食物是中国成功向世界输出的少数文化产品之一。
然而,西方对中国饮食的理解却远未深入。
自19世纪中叶以来,种族偏见塑造了人们对中国食物的负面观感,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
从一开始,当地人对于大块肉类的呈现感到怀疑,认为略显杂乱的切块食材是在掩盖其低劣品质。
许多人还对食物的清洁度产生质疑,担心由“泼皮”们操作的餐厅厨房不够干净。
这些偏见至今仍在,大多数人并不将中国食物与精致的饮食联系在一起。
更为恶劣的是,关于中国食物吃猫、蛇和老鼠等“野蛮”饮食的贬低指控持续流传,尤其在COVID-19疫情的起源问题成为中西关系的一块烫手山芋后,相关说法更是重新浮出水面。
这种中国饮食在西方的存在,既熟悉又被误解,构成了两本新书的背景,这两本书试图加深外国读者对这一主题的理解。
Fuchsia Dunlop的《邀客盛宴:中华饮食的故事》(2023)努力揭穿西方对中国饮食“廉价、低端、垃圾”的常见偏见。
她认为,英美世界中所提供的中国餐馆食物根本与大多数中国人实际所吃的食物无关,且那些在西方从未到过中国的人们对中国美食的想象与真实情况也是截然相反的:健康、精致且高质量。
作为证据,书中每一章讨论了一种菜肴或技术,展示中国饮食的丰富性,从所使用的多样化食材到饮食与医学之间的亲密关系。
例如,稀饭(Congee)简单地用大量水煮米,早在中国就被誉为治疗大多数基本疾病的良方。
邓洛普引用了宋代诗人陆游的说法,他认为食用粥是长生不老的关键——我母亲在我生病时仍以此为我炖粥。
邓洛普的作品在某些部分颇具煽动性,是她为中国饮食在西方辩护的有力论据。
她在1992年到达中国时便是第一位在四川高等厨艺学院学习的西方人,该学院是四川料理的顶尖烹饪学校,四川菜是中国四大菜系之一,近年来在中西方均获得显著的关注。
此后,她写下了多部关于中国饮食的畅销书,包括2008年的《鲨鱼鳍与四川胡椒:在中国的饮食回忆录》和2019年的《四川饮食》。
在如今西方对中国的各种离谱论调中,邓洛普的书会引起那些志于向国外观众解释中国的作者、记者及学者的共鸣,他们也同样对此感到沮丧,认为中国的真实面貌与外国的想象相去甚远。
邓洛普指出,西方对中国饮食的偏见在历史上同样具备重要的影响。
19世纪期间,英国的殖民冒险常常以给“落后”的中国人带去急需的文明为名。
正如1793年一位英国特使所言:“它们喝同一个杯子,虽然有时漱洗,但从不清洗和擦干。”
书中大部分内容庆祝了富饶的江南地区的烹饪传统,江南是中国烹饪的旧发源地,也是邓洛普2016年《鱼米之乡:来自中国烹饪心脏的食谱》中的主题。
该地区以其清淡风味和重视应季饮食而闻名,它的饮食文化不仅深深影响了邓洛普对中国饮食的写作,更在她2000年代中期因在全国各地品尝美食而对中国烹饪感到失望时几乎拯救了她的美食激情。
转折点发生在2008年,当时邓洛普首次造访龙井庄园,这是位于江南中心的一家农场到餐桌餐厅,店主倡导恢复中国的传统饮食文化,如有机饮食和应季饮食。
邓洛普写道,她在该餐厅的第一次用餐让她“在智力和感官上都理解到了最好的中国食物是什么、它曾经是什么,以及它还能成为什么”(强调部分为我的)。
几个月前,我第一次在龙井庄园用餐。
这次经历让我不仅对邓洛普在西方持续为这家餐厅加油鼓劲感激不已,尤其是在其2008年《纽约客》的专题报道中,更让我认同她对该餐厅的评价,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餐厅之一,甚至在中国也是如此。
但当我啜饮丰盛的放养鸡汤,翻阅记录详尽的我们菜单中的成分清单时,我同样惊叹于,这一切与今天的中国年轻城市居民所吃的食物相去甚远,遑论“绝大多数中国人实际所吃的”。
那么,大多数中国人究竟吃些什么呢?
邓洛普赞扬传统中国饮食的健康利益——以大米、小麦和熟蔬菜为主,但这并不是大多数中国人实际所吃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快速的城市化和收入增长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采用以肉类和加工食品为主的西方饮食。
这在体重方面的影响与西方相同:一半的中国成年人现在超重或肥胖,预计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三分之二。
邓洛普清楚这一点,但未能意识到以中国为例来呼吁西方国家“重新思考它们不可持续的肉类消费”,的讽刺。
她写道:“中国厨师的资源fulness可能是充分使用食材和尽量减少浪费的一个范本,”却没有提到中国家庭的人均食物浪费比美国家庭还要多。
缺乏自我反省是她作品中的一个反复问题,例如当邓洛普完全认同自己是个“糟糕的中国饮食谨慎者”时,并将西方饮食习惯与中国进行不利比较。
她早早指出,中国人常常对“西方食物”进行粗略的一般化,而她本身在整个书中却也进行相同的行为,曾在某个地方形象化地将西方饮食描绘为“浸满培根和奶酪的牛肉汉堡”,而另一刻则描述为“胡萝卜和芹菜的棍子”。
虽然理解邓洛普期望为中国饮食辩护的愿望,但她急于声称其优越性并未能让她的书如同一些关于中国最佳历史的作品那样说到当下。
例如,在一章关于蔬菜的内容中,邓洛普声称中国一些最弱势的人群,即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的农村中国人),比“富裕的中产阶级英国家庭”更健康,然而在对目前经济困境时期的讨论中,这样的比较显得荒谬。
中国的三亿农民工中,许多人仅仅在勉强生存。
有关中国饮食的书籍通常面临相同挑战:如何向外国读者解释一个拥有14亿人口和巨大的生活水平差异的国家,其中的生活经历从江南的辉煌到内部移民的日常劳动不一而足。
邓洛普在抵制关于中国饮食的负面叙述时,呈现出一些积极的叙述,却未曾意识到这些叙述本身也是泛化,亦落入了同样的简化游戏。
她写道:“只有中国人将做饭置于自我身份的核心。”然而很显然,讽刺的是,中国政府近年来将支持即食餐行业作为其应对食品安全问题的举措。
同样可以说,过去十年中国的外卖行业也在蓬勃发展,因为愈发艰巨的工作时间使得许多工人再也无法为自己做饭。
如果对这些矛盾进行全面考量,将会使书籍更加深入。
为什么龙井庄园在当今中国如此独特?
为什么其有机食材每人消费的费用甚至超过了许多农民工一个月的食品预算?
邓洛普未能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推测可能是对此主论点不利的诸多答案——食品安全、收入不平等以及竞争激烈的社会——会让她的论据显得不便。
然而这些因素在勾勒读者们一个准确的中国图景时亦至关重要。
托马斯·大卫·杜博斯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他的《七个盛宴:美味历史》(2024)将其食物叙述扎根于深远的历史力量,特别关注金钱与科技对中国现代饮食关系的影响。
这种关注体现在他在后几章所剖析的一些“盛宴”的平凡性质——自世纪之交以来,火锅作为一种家常便饭进入了大片市场。
尽管它似乎并不适合外卖,但其作为外卖菜肴的流行反映了当今城市中国便捷饮食文化的兴起,同时也突显了大量塑料包装对环境的影响,这种便捷性得以通过诸多独立包装的食材和调料来实现。
对于餐馆而言,火锅是一种赢利丰厚的菜品,因为顾客可以自己烹调食材,从而使受过精良训练的厨师及厨房的重要性降低,食材可以简单地在集中设施中准备。
“[T]中国食品的历史不仅仅是关于食物本身,”杜博斯写道,他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
他作为历史学家的训练很为明显,尽管这本书不仅是中国烹饪的历史,更是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下,中国饮食与其间的互动。
与杜博斯关注的七个中国历史上标志性的盛宴相比,邓洛普更多关注单体菜肴,强调了饮食在中国深厚的社会内涵。
古代中国文明早期的典型盛宴是周朝(公元前1046-256年)的“八珍盛宴”,由八道选用昂贵肉食的菜肴组成,记载于儒家经典《礼记》中。
这一盛宴由历代帝王为年龄较大的贵族和平民举办,体现了正逐渐形成的“道德社会”。
杜博斯指出,食物已成为道德纽带的具体现象。
对老年人的尊敬成为了统治者展示其儒家声望的方式。这一盛宴在现代中国社会仍然能轻易找到其相关性:许多菜肴的格式延续了“八珍”的风格,从粥到茶种类丰富,同时孝敬的文化依旧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支柱。
杜博斯的书中交错着数十种百年名菜的详细食谱,从荔枝鸡到宫保鸡丁。
他对展现自己档案工作的显著热情有时导致冗赘的篇幅,特别是一些盛宴的完整菜单(常常翻译难以理解)占据数页。
尽管在中国,详细阅读重要盛宴的菜单是一种典型的消遣,但解释海量同音字和诗意命名的隐含意义在翻译中往往会失去部分或完全变得不可能。
这项烹饪考古的确是值得的,它追溯到一些盛宴可能非常平淡、缺乏香料和调味品,从而重申它们的象征性和社会功能。这包括不仅是八珍宴,还有唐代(618-907年)的“尾焚盛宴”,它被皇帝用于欢迎新官员进入其核心圈子(尾焚象征重生)。
中国的盛宴作为礼仪和礼节的表达,而不单单是物质上的愉悦,这一点对每一个曾在中国做宾客的外方外交官和商人都非常熟悉。
一道道菜品上桌,尽管食物甚至可能非常可口,但用餐永远是次要的。这就是为什么食物浪费在中国特别棘手的原因,因为社交礼仪不仅使浪费不可避免,甚至是展示慷慨的必要。
在两国被卫冕为学者的同时,杜博斯擅长解构中国饮食关系中包含的多重意义。当他剖析真实与虚构的盛宴时,食物被诠释为一个富有隐喻的形象,一种文化遗物,既是意义的源泉,同时又被赋予意义,正如宗教神话的表述一般,毋需历史中的准确性依旧会持续产生影响。
缠绕着这一象征的还有一个同样同样淡薄的盛宴:“满汉全席”,这是满族统治者在清代为赢得周边蒙古人的喜爱而提供的大餐。 尽管关于它的首次出现及其所用食材并无共识,但这个盛宴如今已经成为民族和谐与“伟大民族团结”的国家象征。
正如孙中山,在20世纪初被称为“现代中国之父”,他及其同僚清楚地认识到食物不仅仅是生存的手段,更是讨论其时代危机的重要工具。
在杜博斯的书中,食物同样扮演相同的角色: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既是研究的对象也是方法论。
他书中最有力的部分是利用食物勾画中国社会和政治历史的篇章,例如揭示20世纪以来西方食物影响的复杂存在。
20世纪初的现代化与西方化之间的矛盾在20世纪50年代再度出现,国家出版的食谱笔记状态得以恢复,努力在苏联式乌托邦主义与爱国节俭之间找到平衡。
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西方食物又变回政治修正主义的象征,著名的莫斯科餐厅的命运恰如其分地封装了一个时代的曲折。在1954年开设之时,这个餐厅成为赴苏联卓越典范的神殿,整个国家的工人均发放理补券特地到此用餐,以体验蕴含的奢华与富饶。
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过去,红卫兵们将餐厅强迫转为中国饮食;在80年代回归平静时,顾客对再次品尝俄式食物的期盼又再显露出来。
利用食物作为历史视角的有效性使无专门章节讨论毛泽东时代显得格外明显。
虽然大跃进运动被简要提及,但还有相当空间就此展开,以探讨规定时期内如何将食物作为武器及其遗留下来的影响——即在此政治宣传和国家文件中对食物的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失调。
人们不禁要猜测未能详细探讨这些问题的理由。
这将我们重新引向当今撰写关于中国的讨论。
正如中国饮食应在其更广泛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中理解一样,关于中国食物的书籍也应与其出版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
自2012年习近平执政以来,他强调了需要让中国人民对其历史与文化价值“增有信心”,并对传统中国文化予以重视。
尽管这听上去无害,但这背后传递出一个越来越刻意在战略上界定文化的政权。
在国家内部及其外部推动文化自信的举措,传递对其饮食传统的热情——这一行为是对美国所期望的文化霸权的回应。
若中国展现出丰富的传统和自身的价值,那么我们便无需接受西方的任何东西,比如民主和人权。
在实际操作中,这已意味着对文化活动的监管更加严格,同时对发出简化叙述中国伟大形象的项目的支持——如果可能的话,还能将西方描绘成衰退的国度。
和当下越来越强硬的对待西方媒体及学者相并行,现阶段该政权将其视作西方文化霸权的同谋,而非潜在的解决方案。
因此,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本关于中国饮食历史的新书是由一位英国人和一位美国人写成的——这两位西方人被授予了越来越少的机会去接触中国及其人民。
正如孙中山、习近平领导下的国人所理解,饮食时常是对中国在全球中的立足地位进行深思的地方。
而如今,中国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正不再认为自己“在所有现代文明领域落后”,启示着国家宣扬其不必向西方学习的自信。
因此,当西方人解读关于中国文化的每一个角度时,他们逐渐需要思考他们的工作最终将为谁带来好处,尤其是在涉及到那么简单却文化内涵纷繁复杂的主题——饮食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