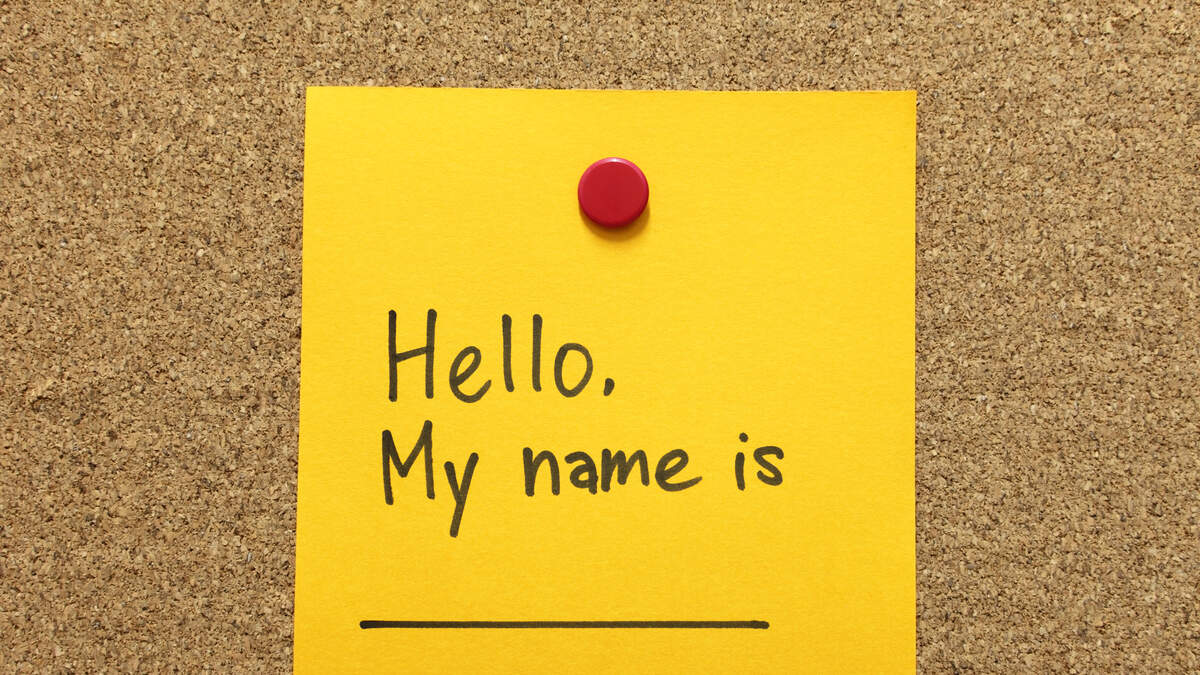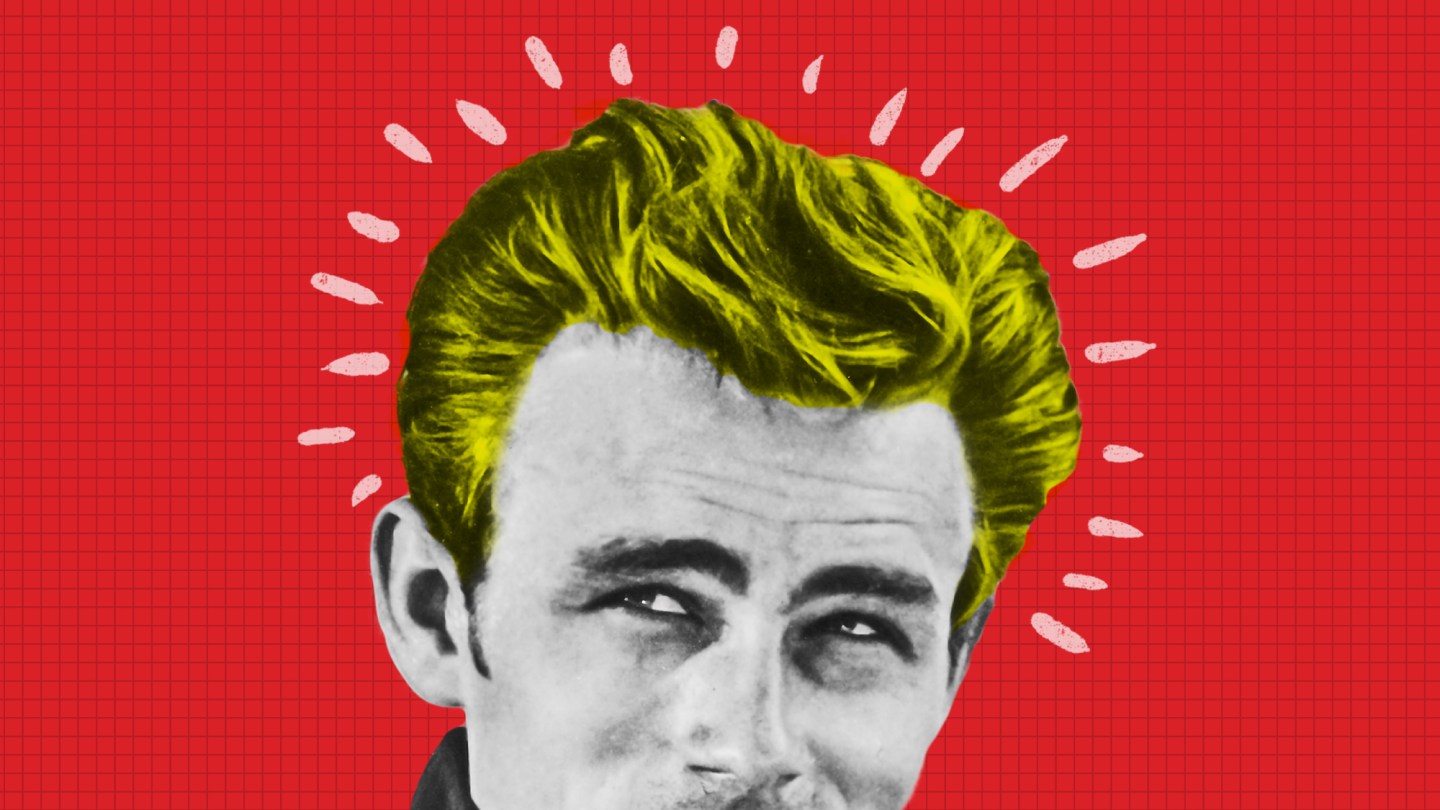在洛杉矶,舞蹈既不是中心,也不算荒漠。虽然我们缺乏培育大型芭蕾舞团的悠久历史,但小型舞团却层出不穷,包括现代舞、古典舞以及国际舞蹈。
无论你在哪里,总有人在这里为你舞动。上周末,我在三个不同的城市和场地体验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舞蹈演出,尽管风格各异,但却有着令人振奋的共鸣。
在舞蹈的高端,迈阿密城市芭蕾舞团在科斯塔梅萨的塞格斯特罗姆音乐厅带来了其近期制作的《天鹅湖》,并将在今夏进行不同版本的演出。波士顿芭蕾舞团将在本周末前往音乐中心。而旧金山芭蕾舞团也将在好莱坞碗贝尔的洛杉矶爱乐乐团的“柴可夫斯基壮观音乐会”中表演片段。
在费尔法克斯区的电视城录音棚,洛杉矶的典型舞蹈公司——美国当代芭蕾舞团,正在演绎乔治·巴兰切恩的现代经典《塞勒纳德》,并推出了由公司创始人兼编舞者林肯·琼斯创作的新作品。同时,在星期六晚上,小提琴家维贾伊·古普塔与舞者雅米尼·卡卢里,在99个座位的西耶拉·马德尔剧院中,融合了巴赫的音乐与印度古典舞蹈库奇普迪传统。
迈阿密城市芭蕾舞团因其由波尔霍伊出身的著名编舞家阿列克谢·拉特曼斯基执导的“历史信息化”的《天鹅湖》而备受瞩目。他尽力重现1895年在拉特曼斯基的故乡圣彼得堡的马里因斯基剧院上演的版本。
“历史信息化表演”(HIP)这个术语十分复杂,而《天鹅湖》本身也是一部承载了复杂意义的芭蕾舞剧。历史信息化表演起源于早期音乐运动,这一运动试图重现18世纪亨德尔歌剧的表现方式,通过使用古典乐器和被认为是古老的实践技巧,结果却让人们觉得乏味。从而发现,以活泼、富有想象力、现代的方式演奏古典乐器能让音乐焕发出新的生机,尤其是在令人惊讶的现代舞台上。
拉特曼斯基重构的《天鹅湖》在现代乐器与传统芭蕾之间展现了一种反向思维。周日夜晚,太平洋交响乐团在昏暗的大厅中演奏出绚丽华美的柴可夫斯基序曲,意在引导我们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然而,现代乐团和观众手机的刺眼亮光却不断提醒我们,这里是2025年。
19世纪晚期的乐团拥有更轻快、活泼的乐器音色,这与当时的舞蹈风格不谋而合。然而,当周日的帷幕升起,面对古老的布景、服装、编舞和演技,这种风景却如同走进了一家廉价的古董店。
尽管如此,拉特曼斯基却有很多值得称道之处。回溯到1895年,事实上可以表示新生。《天鹅湖》并没有一个定义明确的版本。柴可夫斯基在1877年的首次版本后进行了修订,但在完成1895年的标准版本之前就去世了。因此,编舞者、舞者、制作人甚至作曲家,都为其增添了各自的理解与表现。而在最后,《天鹅湖》的结局可以是辉煌的,也可以是悲惨的。西格弗里德与他的天鹅新娘奥黛特,单独或共同,可以选择生存或沉溺。这部芭蕾舞剧已变得如此熟悉,以至于现代的点缀与其本身相较,便成为了负担。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拉特曼斯基对现代性的回归妥协,是重新思考不仅仅是这部标志性芭蕾舞剧本身,更是重新审视芭蕾舞及其独特之美的起源的优秀起点。两个天鹅的舞段展现了无华的优雅。
西格弗里德的乔治·卡塔扎罗身手矫健,运动感十足,而萨曼莎·霍普·加勒则展现出天真无邪的奥黛特与生机勃勃的奥黛莉,令舞姿如同奇迹般动人。西格弗里德的冲动飞跃,以及黑天鹅的32个旋转,都蕴含着深刻的意义,其余的则显得是分心。
正是在此,巴兰切恩在四十年后的1935年所采取的下一步思想,更是创造了《塞勒纳德》。在《塞勒纳德》中,他以柴可夫斯基的《管弦乐小夜曲》为音乐背景,创作出不再讲述故事的崭新芭蕾舞作品,独具震撼之美。
尽管美国当代芭蕾舞团没有提及,但巴兰切恩于1938年搬至洛杉矶,恰好是在《塞勒纳德》的美国首演三年后,住在距离电视城仅数个街区的住所。在他短暂的好莱坞岁月里,为全球的舞蹈电影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然而,在黑暗的录音棚中,ACB似乎对电影有着浓厚的兴趣,舞者像黑白电影中的角色一样被灯光照亮。由于观众坐在离临时舞台很近的看台上,乐手在观众后方隐身,舞者的表演更增添了亲密感,暴露了复现巴兰切恩舞步的确切努力。我们既在这个瞬间又走向未来的表现效果由此彰显。
《塞勒纳德》之前,首次上演了林肯·琼斯的新作《厄罗斯》和乐章,作曲家是阿尔玛·德伊切尔。这位20岁的英国作曲家、钢琴家、小提琴家兼指挥,10岁时便创作了第一部歌剧《灰姑娘》,并在加州其他地方首演。其首个芭蕾舞作品《厄罗斯》和乐章同样展现出了时间旅行的主题。
每个变奏都代表一位古希腊女神,体现出维也纳华尔兹曲调在弦乐和钢琴的伴奏下的独特魅力。尽管德伊切尔运用了现代手法来揭示每位女神的特质,但其旋律让人仿佛置身于柴可夫斯基的年代。在这一舞蹈中,琼斯运用来自巴兰切恩的舞蹈词汇,为每位女神舞者以及最后的男主角创造了舞蹈语汇。在这里,历史归根究底又超过了全新舞台的表现,在这个时尚的当代环境中,古老与现代试图交织出一幅华美的画卷。
古普塔在其辉煌的《当小提琴体会爱情》中恰到好处地调和了古与今之间的关系。他的表演表面上展现出一种有趣的文化交流。他一边演奏巴赫的独奏小提琴《帕蒂塔第2号》和《奏鸣曲第3号》,一边与卡卢里一起探索如何在个别乐章中表达情感或找到节奏活动。她穿着现代服装,与音乐亲密相融,展现了不同时期之间的桥梁。
古普塔自2007年以19岁加入洛杉矶爱乐乐团以来,被广泛熟知。他创办了街头交响乐团,服务于无家可归者和被监禁的社区,还成为了一名鼓舞人心的TED演讲者。他获得过麦克阿瑟奖,自从离开洛杉矶爱乐乐团以来,他在当地的室内乐节目中频频亮相,并在洛杉矶音乐团体Tesserae中以巴洛克小提琴与大家分享音乐。
在《当小提琴体会爱情》中,古普塔运用了现代乐器,并以高度表现力的当代表达形式演奏,仿佛在将一段萨拉班德转化为拉伽。他停下脚步朗诵诗歌,无论是苏非诗还是里尔克的作品。他的音调宏大、鲜明且引人入胜,尤其是在这个小剧院的优良声学环境下。巴赫的作品则通过作曲家瑞娜·埃斯梅尔为《当小提琴体会爱情》创作的感人独奏作品相连,仿佛巴赫、印度音乐与库奇普迪舞蹈都来自同一深切的归属感。
仅需一位小提琴师和一位舞者,就能展示出尽管舞蹈的跨度庞大,但这些联系却是不可避免的。
图片源于:la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