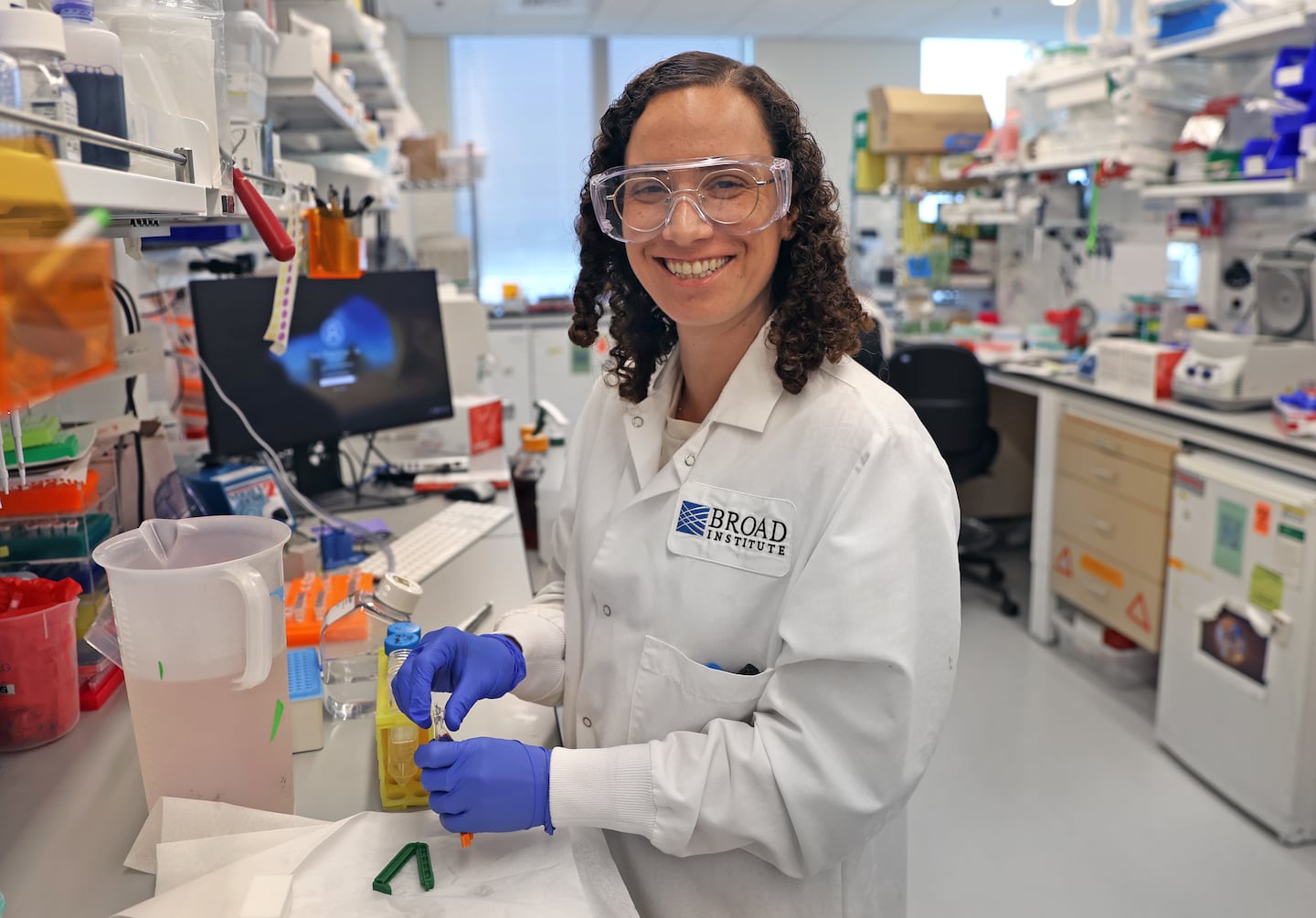图片源于:https://sampan.org/2024/boston/adoptees-torn-over-chinas-end-to-overseas-adoptions/
当艾米莉·范·沃尔金堡(Emili Van Volkinburg)在九月初得知中国结束国际收养时,她感到矛盾。
作为25岁的布莱顿居民,她在两岁半时被来自俄亥俄州的白人父母收养。她的成长过程中,母亲与她们进行过开放的对话,讨论收养的话题。父母还为她和她的亲生姐姐(同样来自中国的收养者)报名参加汉语和文化课程,以保持与中国传统的联系。全家一起上舞蹈课,母亲还学习如何烹饪亚洲美食。范·沃尔金堡表示,在大部分时间里,她对自己的收养经历持积极态度。
在成年后,她与其他华裔及跨种族的收养者建立了联系,意识到他们的成长经历各不相同。她提到,许多白人父母在养育不同种族和民族的孩子时面临着困难。这让她开始思考收养对其他人的不同影响。
“可能有很多家庭在收养中国孩子时并没有考虑到对自己和孩子的后果,或者没有考虑到这对孩子未来的文化影响,”范·沃尔金堡说。
如今,似乎范·沃尔金堡成为了和她一样的最后一代中国收养者。随着该项目的结束,她希望这能引发关于收养的更深入对话。
在九月初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确认,中国不再允许外国收养儿童,称这一决定符合“相关国际公约的精神”。她表示,只有在中国的外国人收养血缘亲属的子女或继子女(亲属关系至三代内)才可例外。
这一决定标志着为期三十年的收养项目的结束,这一项目导致至少10万名像范·沃尔金堡一样的中国儿童被收养到其他国家,其中超过82,000名被送往美国。
中国的收养项目始于1992年,之后因1979年出台的有争议的单独政策开始。由于人口过剩,许多孤儿都是女孩或有残疾的儿童,他们被送去收养,因为这一严格政策与对男孩的文化偏好相结合。
近年来,随着中国在2016年逆转政策以应对出生率下降的经济和政治挑战,收养的数量逐渐减少。在2020年疫情高峰期间,中国暂停了两年的对美国的收养。在2021年,中国宣布实施“三孩政策”,通过延长产假和住房补贴等激励措施来应对日益减少的人口。
家庭纽带超越血缘
安东尼亚·马丁-努卡托拉(Antonia Martin-Nucatola),24岁,来自牛顿,自小对自己和非亲生姐妹的收养问题充满好奇。她常常问父母她们的出生地,填写的纸质文件是什么,为什么更多的女孩被送去收养。
她的父母非常坦诚地与她们分享关于收养的经历。
他们也让家庭沉浸于中国文化之中。一起学习中国生肖、农历新年和中国美食的时光加强了他们之间的联系。
“这些是我童年中的强大时刻,让我非常感动,”马丁-努卡托拉说。“我想到我的母亲,她曾经参加我的中国舞蹈演出。她是唯一的白人母亲,与所有其他中国妈妈在一起……在那个空间中,她是少数,但她这样做是为了让我理解文化。”
收养项目的最新发展让马丁-努卡托拉开始思考,如果自己没有被收养,生活会是怎样。
“我心里的一部分在想,可能有孩子可以从我和我姐妹所拥有的特权中受益,因为我们被世界上最好的父母收养了,”马丁-努卡托拉说。
她对那些困在孤儿院中的孩子,或是那些待处理申请的美国家庭感到担忧,这些人现在陷入了未知境地。中国没有提供关于那些孩子未来会怎样的任何细节。
“我对此感到非常沮丧,因为中国政府在一个真空中做出了这一决定,完全没有考虑到对所有相关方,尤其是对收养者和孩子们产生的损害影响,”31岁的妮可·艾格布雷特(Nicole Eigbrett)说。她在1992年收养计划开始时被收养,回想起此计划也让她感受到被抛弃的情绪。她在纽约的一个以白人为主的城镇长大,父母均为白人且中产阶级,同时养育了收养和亲生的孩子。她是家庭中唯一的亚裔。
“制度化的抛弃”
艾格布雷特回忆自己一生的经历,寻求社区和归属感的模式始终如一,她从小在小城镇经历了种族歧视和民族孤立。2016年她搬到波士顿后,寻找亚裔美国人社区以便联系。通过这一过程,她成为了波士顿多切斯特的非营利组织“亚裔美国人资源工作坊”的志愿者。该组织支持大波士顿地区面临驱逐风险的泛亚裔社区,提供服务,倡导面临驱逐的社区成员,并推动年轻亚裔及太平洋岛屿居民参与公民事务。在该组织中,她遇到了志同道合的政治理念及其他收养者。
除了对收养项目结束的悲痛和担忧,艾格布雷特也感受到一种解脱,认为中国孩子不再被迫与生物家庭、故土和文化分离。艾格布雷特是收养废除运动的一部分,该运动呼吁以广泛的生育健康护理、经济福利和社会支持来替代收养或“制度化的抛弃”,以照顾全球范围内的家庭。
“普遍存在的观念是,收养会自动给孩子带来更好的生活,”艾格布雷特说。但许多人经历了与收养相关的痛苦和创伤。
这种观念还意味着所有亲生家庭都无法为孩子提供足够好的生活,29岁的玛雅·伯加马斯科(Maya Bergamasco)也对此持同样看法,来自梅德福的她对中国停止收养项目感到高兴,并希望中国能够对当前困在孤儿院的许多残疾儿童提供支持。
艾格布雷特指出,与其提倡收养,中国等国应为公民提供充足的资源。
伯加马斯科希望这一禁令促使中国政府承认收养社区是中国侨民的一部分。通过这样的方式,收养者能够获得特殊签证或更清晰的中国国籍途径。
与此同时,她表示,这一消息可能会让更多的收养者“走出迷雾”,指的是收养者反思自己收养经历对自我的影响的多层次过程。自此后,她与有着相似经历的人更加亲近,并渴望提升他们的故事。
“在历史上,我们是一个有被遗忘风险的代际群体,如果文化保护和故事讲述没有得到重视,”伯加马斯科说。
这些叙述必须由收养者自身主导,她继续补充说,历史上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伯加马斯科认为,收养者的声音往往被贬低,而收养父母则更为突出。
“我们也应当拥有一个与收养父母迄今为止所拥有的声音和平台,”伯加马斯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