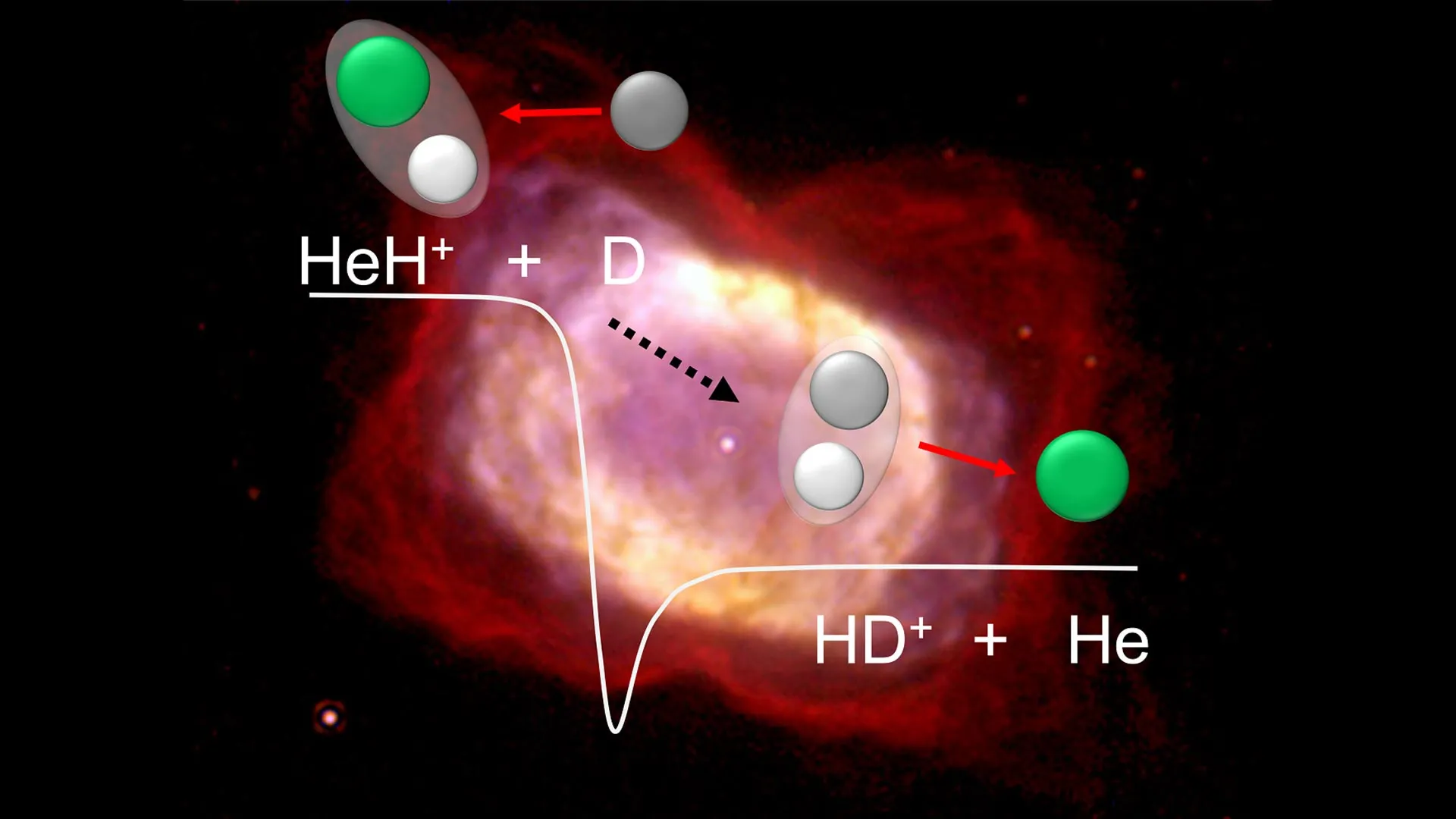图片源于: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9-025-04529-0
近日,有研究发现,印度媒体对中国双碳承诺的论述呈现出多元化特点,涵盖了环境、政策、经济和技术等多方面内容。
研究还暗示,这种论述与印中双边关系密切相关,着眼于对中国环境政策实施及其影响的批判性审视。
具体而言,研究的核心部分指出,当前“气候行动”需要考虑并实施财政和技术支持,尤其是对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全球显著的碳排放国,必须采取行动并对减少碳排放负责,最终实现净零目标。
在表1和图2中展示了高频词列表及其共现网络。
图2中以“中国”为中心的网络结构,显示出“中国”和“印度”是该话语中关注的核心,表明两者在媒体报道中的重要性。
“气候”、“排放”、“碳”、“净零”等词语则强调了环境问题的重要性,这是主要讨论的话题。
而“目标”、“计划”、“行动”、“承诺”、“中立”等词则指向政策制定和行动计划的讨论。
与此同时,“年”和“时间”突显了实现双碳目标的时间线和计划的必要性。
此外,“财政”和“技术”则指示了与承诺相关的财务和技术考量,这与核心部分内容相对应。
由于政策/计划和时间安排大多与中国有关,因此可以推测中国在处理化石能源消耗方面已做出具体安排并公布了详细的时间表和计划,从而实现能源转型。
因此,中国的双碳承诺被视为一项复杂而多面的计划,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印度媒体特别关注的承诺具体方面。
换句话说,位于“中国”或“中国的”后面的内容大多是与中国双碳承诺相关的特定子主题,即探索在将“中国”或“中国的”作为核心时的共现网络。
通过将语料库和高频词输入KH分析器进行处理,发现相关报道主要涉及四个部分,这在图3中得以展示。
该图以“中国/中国的”为核心词,通过模块化网络识别了该语料库关注的特定主题。
从图中可以观察到,所生成的不同颜色的节点组展示了与“中国/中国的”相关主题的集中程度和其关系的强度。
图中四个主要分支以不同颜色呈现,左侧分支指向中国双碳承诺的公告背景,包括“全球气候危机”、“新冠病毒造成的经济衰退”、“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排放国”等。
上方分支则展现了中国的碳中和目标和计划时间,即到2060年实现净零。
而下方分支集中于中国实现这一目标的详细行动计划,即“调整化石燃料的使用”、“进行能源转型”、“管理用电结构”的措施。
右侧分支则关注中国实施这一策略所需的前提条件/能力,如“财政”、“技术”等。
因此,印度媒体对中国双碳承诺的具体主题可以被识别为:(i) 目标/目标,包括承诺的目标和实现双碳目标的时间;(ii) 计划,包括实现目标的政策、行动、措施及其带来的效果;(iii) 实施目标的条件或能力及相关潜在问题。
在话语策略和语言手段方面,定名策略是关键。
如前所述,定名策略指的是对涉及双碳承诺的人员、物体、现象/事件、过程和行为的命名和引用。
具体而言,这项策略专注于探讨与双碳承诺相关的行为者的语言表现。
研究发现,印度报道主要将中国呈现为两类行为者:作为权威的中国和中国公司。
表2展示了这些反复出现的引述术语。
例如,除了常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报道中还引用“(中国)政府”、“(中国)主席习”、“北京”等专有名词以及一些集体名词如“主要/最大的排放国/污染者”等。
在对相关语料库和广泛文本的进一步探讨中,这六种定名在三个子主题中存在独立联系,表3中做了标示。
“(中国)主席习”这一称谓在社会性行为定名策略的语篇构建中可能被视为一种转喻性引用,具备以下转喻意义:领导者代表国家。
通过对共现线的审查,此类提法与“中国双碳目标”中的“目标”频繁共现。
例如(1)与(2)中指出:“中国主席习金平承诺将在2030年前实现国家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报道将习主席呈现为中心行为者,强调他在应对气候变化排放方面的承诺。
而“承诺”一词则突显出个人的责任感和权威性。
通过将其描述为“承诺”,该报道强调了主席的个人义务和决心,使其在国家战略中充当关键角色。
在后续示例(2)中,将主席习金平的声明解释为对中国排放轨迹的目标,使用“目标”一词暗示了战略目标。
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引用总统,意图强化其在塑造国家战略中的推动作用,构建起行动和承诺的主导形象。
相较于使用“中国”或“中国政府”作为主语,报道突出个体的能动性和决策能力,暗含个人的参与和责任。
这将实现权能化、问责性和战略传播的功能:“赋权”不仅强调了领导者在应对关键问题上的主动性;同时也使其承担起实现既定目标的责任。
再者,此种的叙述简单化了复杂叙事,使公众更易于理解(Bunders et al., 2021; Palmieri and Mazzali-Lurati, 2021; Zhang and Orbie, 2021)。
然而,这样的构建可能会引发关于过度简化复杂决策过程或忽视专家、顾问和机构等集体性努力的争论。
因此,这种对碳承诺的构建依赖于较为简单的逻辑,可能会掩盖参与决定的重要集体决策过程(Franks et al., 2003)。
示例(3)中出现的表述同样如此。
例如:“习主席承诺将在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承诺”一词突显了政治领导者的权能,增强了领导者的个人重量感,也加强了外界对中国双碳承诺的负面看法。
至于“计划”,报道主要关注实施效果,以判断国家战略的理性。
这也借着对“北京”的关注,以指涉中国的首都,作为国家的代名词。
在这个过程中,印度媒体倾向于简化有关能源管理和气候变化的复杂问题,可能使矛头指向单一实体,影响公众对政策有效性的看法。
例如,报道指出:“…在9月和10月,中国面临严重的能源短缺,部分原因是煤炭公司减产以满足北京的气候变化承诺。”
该段落描述了煤炭生产削减造成的影响,显示了中国在实现碳中和过程中实施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最后,示例引发指责,归咎于北京在双碳政策上的承诺与实施,从而贬低了整个执行方案。
在“条件”方面,印度媒体意图标记中国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即强调其负面属性,以提出其完成双碳目标的能力,潜在地忽略该国的其他努力和特质。
例如(5)中表示:“相较于世界最大排放国家,其行动将会更加进取,直到1900-2100年,印度的累积排放量会低于中国的。”
(6)中则关注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碳污染者”,表明公众对中国能够完成气候承诺的质疑。
这样的特别定名对参与者的感知产生了深远影响。
示例(5)将中国视为“最大排放国”,强调了其在国际气候危机中的贡献。
而“累积排放量(1900-2100年)”这个叙述则从历史和未来的角度添加了公正和责任的感觉,影响了受访者对舆论的解读。
示例(6)中的“世界最大碳污染者”则暗示了对中国的负面和批判性评估。
通过这样表述,媒体能够影响观众对中国在全球排放中角色的理解,暗示了中国作为显著的负面因素筷饼,形成紧迫感或指责,导致公众对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能力产生疑问。
最后,这样叙述会将中国,作为排放的庞然大物,置于发达国家与低排放经济体的对立位置,使得中国被分为缺乏实现碳中和目标能力的国家,与持续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的其他国家形成鲜明对比。
综上所述,印度媒体突出了中国作为主要碳排放者的形象,质疑其实现气候承诺的能力。
这种策略简化了叙述,并可能影响公众对气候行动和责任的认知和国际话语。
然而,少数报道中使用了人名,解释并捍卫中国在实现目标中的困难。
例如(7):“作为世界最大煤炭生产和消费国,中国更倾向于倾向于渐进式减少而非彻底消除。”
“可以理解”的表达抓住了中国妥协行动,这暗示了对其现状的同情和理解。
因此,并非所有媒体报道都是消极呈现中国的双碳承诺。
最后,可以得出结论:印度媒体利用定名策略来塑造中国在双碳承诺中的形象,意图在决策者和公众之间、地区和首都之间造成一种明显的分歧,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该战略的合法性并形成负面舆论。
其次,预测策略是指通过叙述性地修饰社会行为者、事件、对象等,课程分析进行权利的构建。
这些评估属性助推了对不同引用名词的理解和价值反映。
根据定义,分析着重于高频的评估词或搭配,它们作为上表中引用名词的修饰语加以体现。
表4展示了主要引用的评估归属。
正如所示,印度媒体通过混合的叙述性修饰方式构建“中国”,“中国政府”等名词时采用了中立、陈述性修饰,诸如“交付气候计划”、“承诺达到碳中和目标”、“致力于净零目标”的修饰
还有负面修辞:“占用73%的碳空间”(示例8),“被认定为高效不足”(示例9)以及正面修辞“承诺…是一个重大突破”(示例10)。
示例(8)中,报道称:“…中国的碳排放将在2012-2030年之间占到全球排放的29.5%.”
这意味着国家迅速成为发达国家后,自1949年以来中国市场的对全球发展空间的占有。
这样的描述无疑将中国置于不仅对发展中国家,而且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处于对立面,说明其不仅无碍,更未考虑对其他国家发展空间争夺的可能。
同时说明这种构建可能会引导公众认为,中国实施的双碳承诺将正是要继续占有排放空间,从而使得该国在国际上就是减少碳排放的合理性。
示例(9)则提到,尽管中国已声明将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但其分类为“高度不足”。
这一表述毒化了对于中国能否实现目标的期许,摆布外界对其气候行动的可靠性和真诚度存疑。
可见其构建属于“以权威”声音为前提的妄论,很难仅凭这一语位贬抑国家整个战略,此外该“权威”的声音是否客观也令人质疑。
尽管如此,诸如此类报道中产生的负面语意场及想象,形成了对中国扩大的形象描绘但缺乏合理性,置于严格的批评当中。
而少数报道则对中国宣扬表示赞许,例如示例(10):“中国的承诺…是一个重大突破,尤其是当各国对长期承诺表示犹豫。”
这句话对于中国的“目标”进行了赞赏,考虑到当时全球的气候环境,“并不完全不可行”。
上述两者对目标的描述呈现出固有的高期望。
例如示例(11)反映了在环境陋境下,原先“雄心勃勃”但显然会抑制中国的气候目标。
而示例(12)则质疑“他并没有说明他实现这极其雄心勃勃目标的计划。”
无论从目标达到时间还是实施可以看出,后者充分表明这种构建了负面推理,质疑中国的计划是否合理。
最后,印媒在中国所提出的计划中负面的修辞表现着公共对其执行过程的批判,也给出许多负面特质。
例如(13):“新报告称,‘中国的碳中和目标意味着计划不能继续扩建煤电。’”
此句中的“雄大”又暗示中国允许惑的指责。
在对(14)指出“北京必须燃烧更多的煤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并平息对停电的不满”的时候,强调北京计划实施过程中造成的公共不满。
报道认为北京“令人失望”(示例15),加深了对中国政策的负面印象。
同样集体群体如“互联网/科技公司”,在示例(16)中:全球气候目标出现问题,暗示它们在项目实施中未能积极响应。
最后,在对中国社会及其科技公司提到“不断上升”中,展示了对政策目标背后实现困难的消费力并进一步将负面印象传播,暗示着预期事件的不确定。
综上所述,印度媒体借用定名、预测及视角化策略对中国在应对及落实 碳中和中的形象进行了构造,结合不同的评估归属呈现出复杂且带讽刺性质的对立图构。
同时,尽管在全球最大的排放国家占有位置,但印度媒体认为中国在促进全球气候行动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明确表现为对公众观念和国际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