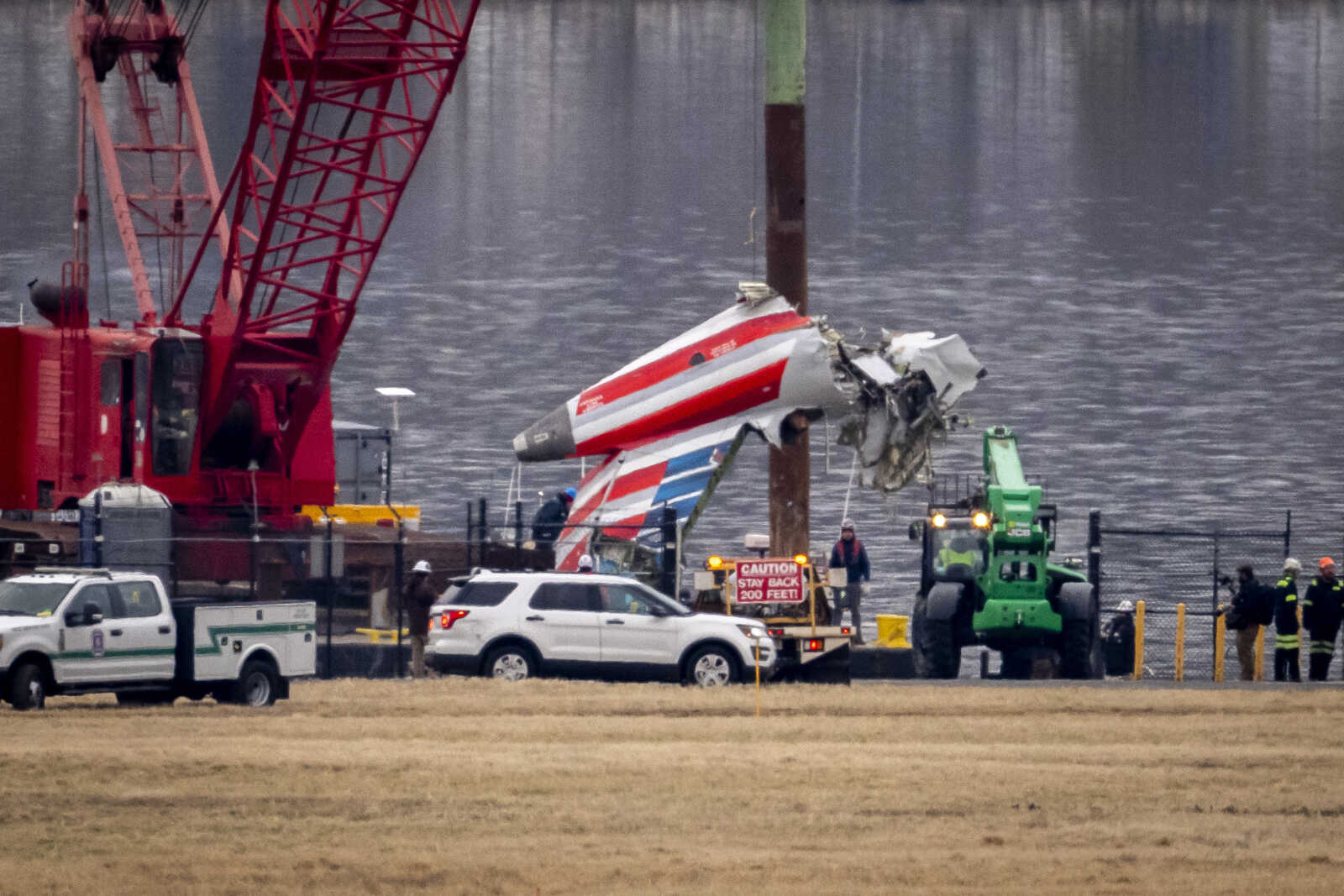图片源于: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curbing-chinas-influence-new-syrian-government
在对维吾尔武装活动的担忧与对扩展与叙利亚商业关系的期望中,北京正在迅速适应大马士革的新现实。
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崩溃不仅颠覆了叙利亚及其邻国的局势,也改变了诸多外部势力在争夺地方影响力的游戏规则。这其中包括中国,北京在与阿萨德政权的关系中,通过提供外交掩护,展现了自己作为叙利亚国家主权捍卫者的形象,以反对外部干预。作为回报,北京获得了关于参与自2011年开始的武装叛乱的中国公民的重要信息,其中许多人来自在国内遭受严重镇压的维吾尔穆斯林少数群体。
这一互利的动态在去年12月被打乱,北京目前正试图如其他各方一样进行重新调整。在阿萨德政权倒台一周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对局势“深感关切”,呼吁采取紧急措施以防止“恐怖和极端势力利用混乱”。然而,仅仅两个月后,王毅就派遣中国大使施洪伟与叙利亚临时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会面。的确,中国官员在这一流动的局势中表现出了显著的灵活性,这不仅反映出叙利亚对北京的区域重要性,也体现出中国对美国在黎凡特地区潜在利益遭干扰的密切关注。
中国对叙利亚政策的演变
在阿萨德倒台之前的多年里,北京以多种方式展现了对阿萨德政权的坚定支持。自2011年以来,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投出的十四次否决中,有八次是与俄罗斯共同支持阿萨德的举动。北京对该政权的例行外交掩护还包括在2023年接待阿萨德及其家人,双方签署协议承诺“共同捍卫国际公正与正义”。
这一做法实际上是中国在中东政策上的一次修正。当阿拉伯之春运动于2010年在该地区爆发时,北京对此持谨慎态度,不愿采取可能被视为支持民众抗议的立场。相反,它公开宣扬其一贯的外交政策原则,即“不干涉”和“尊重主权”,而这一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外部支持的内部起义所产生的恐惧。
然而,利比亚的发展很快考验了这一立场。2011年3月,北京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决定,在投票中选择弃权,批准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为北约对穆阿迈尔·卡扎菲政权的干预铺平了道路。在随后的混乱中,中国公司遭受数百万的损失,官员们不得不紧急撤离近三万名中国公民,这导致一些评论员在国内质疑政府在该地区的政策前后一致性。当安理会六个月后提出要求叙利亚政权停止对平民攻击的决议时,北京则行使了否决权。
中国支持阿萨德的另一主要利益与国内形势密切相关。在叙利亚内战之前,中国新疆省的反政府抗议和民族冲突导致数百人死亡。在随后的镇压中,成千上万的维吾尔穆斯林——他们在新疆占少数——逃往阿富汗、巴基斯坦、土耳其及其他国家,其中许多人加入了像土耳其伊斯兰党(TIP)和伊斯兰国(IS)这样的泛国籍武装组织。当这些组织的成员参加了针对阿萨德的叛乱时,维吾尔外国战士也随之加入,估计在战争爆发几年的时间内,数千名维吾尔战士在叙利亚出现。
2015年,北京警告这些战士正在“被招募非法出境”,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接受“恐怖培训”。到2016年,中国与叙利亚官员每月举行情报共享会议,以追踪这些激进分子。在北京看来,维吾尔招募者正在“等待时机”返回国内,构成潜在的国内威胁;的确,许多战士表示希望利用他们的新战斗经验对抗中国政府。
在新大马士革中的中国利益
最初,阿萨德的倒台加剧了北京的恐惧——反对派不仅真正推翻了政权,而且还有维吾尔战士在其队伍中。部分战士现在在新政府中担任重要职位,其中包括几位TIP指挥官,他们被晋升为新国防部的军官。维吾尔人还被传言是沙拉总统亲信卫队的关键组成部分,这个保安部队还包括来自中亚和高加索的外国战士。
为了应对这些担忧,中国对新政府采取了双重应对。一方面,它谴责维吾尔战士的显著性。去年12月,中国官员承诺,“加强与国际社会成员的反恐合作,坚决打击”这些战士;在今年3月,北京要求叙利亚新领导人“履行反恐义务”和“采取果敢措施”来打击TIP。
另一方面,中国重申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254号决议的支持,该决议呼吁叙利亚主导的政治过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它之前对2254的支持要求各国与叙利亚政府(即阿萨德政权)“保持合作”,而其最新声明则仅呼吁根据2254的“精神”进行过渡。
沙拉的平衡行动
自掌握大马士革以来,叙利亚新领导人正积极进行外交攻势,以获取国际支持,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600场的外国接触。然而到目前为止,只有四次与中国的接触:
早在2月初,叙利亚与中国贸易代表团举行会议,讨论加强双边贸易合作的方式。
在2月底,大使施洪伟与沙拉总统及外长阿萨德·沙伊巴尼会晤。
在3月底,施洪伟与沙伊巴尼的再次会晤中,大使“重申了国家对叙利亚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的尊重”,承诺对叙利亚内部事务“不干涉”,并“强调其在过渡期内支持叙利亚成功克服当前局势”。
在3月中旬,叙利亚农业部长与叙中合作协会的代表团举行会议,讨论农业部门的投资机会以及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策略。
这些初步努力重新建立政治关系与拓展商业利益,表明北京可能采取与美军撤出阿富汗和塔利班重新掌权后类似的务实方针。自那时起,中国在与阿富汗的政治和经济接触中远比其他任何国家更为积极,尽管塔利班过去曾是TIP的关键合作伙伴。这一系列活动很可能源于来自阿富汗的威胁比来自叙利亚或其他中东战场的威胁更为靠近家园。塔利班多次向中国和其他国家保证,阿富汗不会成为外部行动的发源地。尽管关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ISKP)对中国外交官和商人的袭击,这一承诺未能全面兑现,但没有迹象显示TIP成员利用阿富汗领土来策划对中国的阴谋。
叙利亚新领导人来自海亚特·塔赫里尔·沙姆(HTS)组织,但他们的记录显然比塔利班的极端主义少得多。他们还将外籍战斗人员参与外部行动视为红线;例如,1月14日,他们命令逮捕一名呼吁推翻阿拉伯埃及总统一名的埃及战士。
然而,在过去一个月中,TIP发布了一份更新的章程,宣布恢复原名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ETIP),这意味着它将再次专注于新疆。为此,新章程强调中国,同时淡化在过去二十年里使该组织易受全球圣战主义问题影响的议题。在许多方面,该组织似乎受到塔利班和HTS采用的成功政治圣战主义模式的影响。虽然这一转变在实际应用中仍难以预测,但ETIP的变化无疑将影响北京对维吾尔外籍战士在阿富汗和叙利亚的担忧。
政策影响
尽管中国与后阿萨德叙利亚的接触数量相对较少,但它的确表现出改善关系的明确愿望,尽管对新政府中的维吾尔武装团伙仍存在担忧。如果华盛顿继续其对新叙利亚的温和接近,可能会让北京更容易实现这一目标。历史上,俄罗斯曾是大马士革的更传统盟友,但现在在经济实力上已经不如中国潜在提供的支持,特别是在叙利亚经历了十四年的战争,迫切需要经济增长和重建援助之际。
为了关闭北京在大马士革可能存在的潜在机会,华盛顿应制定合适的接触计划,专注于与沙拉的临时政府合作,缓解制裁,并根据第24号一般许可延长豁免,以促进更广泛的经济机会。这不仅会激励新政府向西方靠拢,也将阻止中国在这个重要的中东国家采取潜在的破坏性进入。
Grant Rumley 是华盛顿智库的梅泽尔-戈德伯格高级研究员,并是其戴安娜与吉尔福德·格雷泽基金会大国竞争与中东项目的主任。
Aaron Y. Zelin 是该研究所的莱维高级研究员,著有《政治圣战时代:海亚特·塔赫里尔·沙姆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