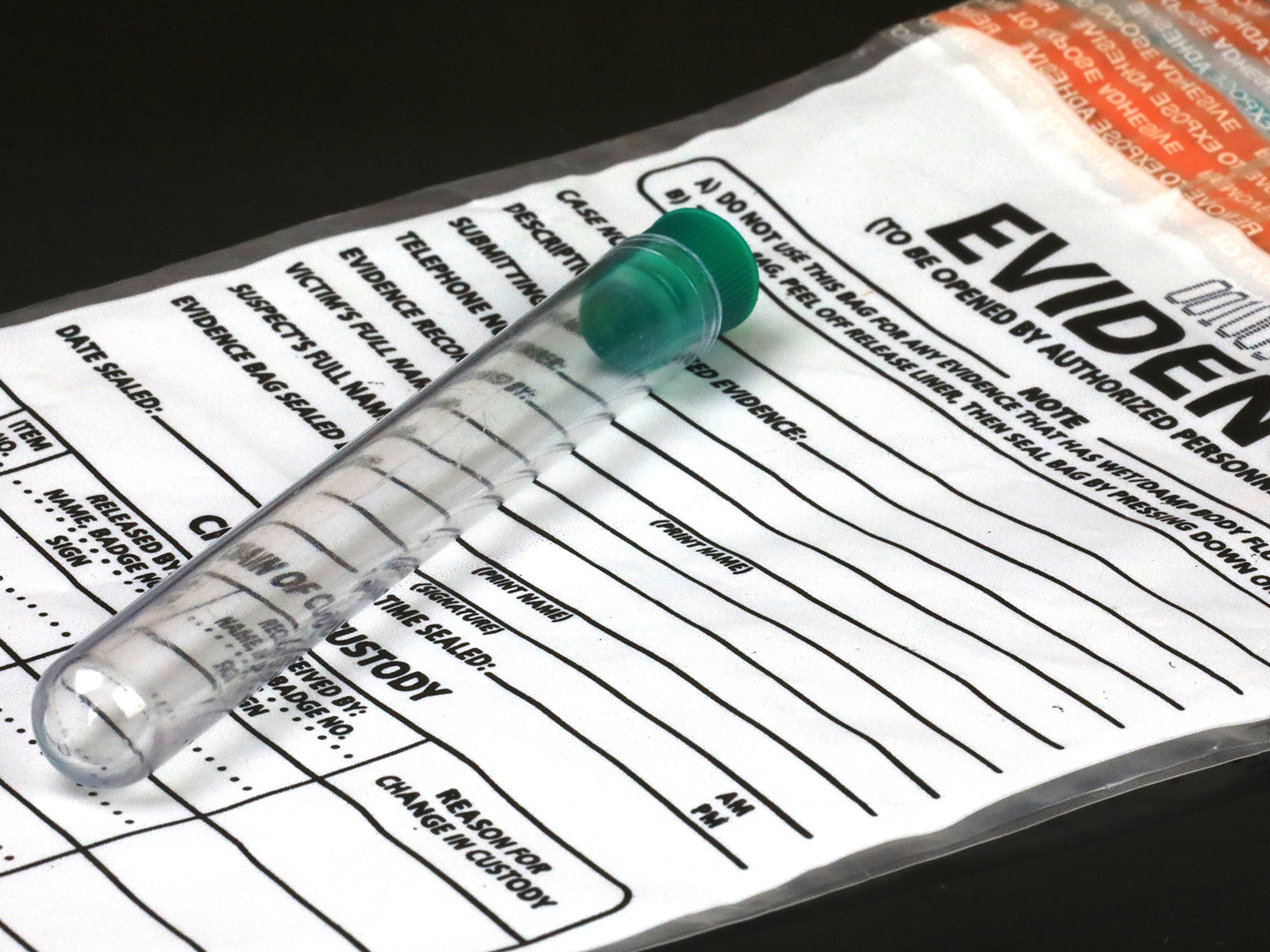在阿拉巴马州外的小镇长大,周围人们唯一引以为傲的事情就是我青少年时期开设的星巴克。我的成长过程中没有看到任何同性恋的榜样,周围的单一文化只透出一幅幅夸张的刻板印象。在迪士尼电影里,他们往往是反派;在情境喜剧中,他们则滑稽可笑。这样的环境使得同性恋被视为错误、可耻、甚至是邪恶的。
在母亲的支持下,我直到15岁第一次性经历时,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是同性恋,那一刻是我真正的觉醒。进入大学后,我深深融入了同性恋文化——《同志如我》(Queer as Folk)、夜总会、骄傲活动,我的身份围绕着派对、渴望和寻求认可而建立。
为准备骄傲活动,我节食,过度锻炼,甚至采取激素,希望能达到自我爱的理想状态,但这种状态从未实现。那时的骄傲对我来说并不包容,而是一场流行的选美比赛。我没有意识到,作为一名白人男性同性恋者,我拥有的特权是多么有利。而我内心里面,总是厌恶自己的倒影。
许多人并不知道,同性恋者自出生起就承受着外界的评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外部的评判常常内化,塑造了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和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要解构这些叙事,时间是漫长的斗争。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视角逐渐清晰。参与的派对变得空洞,我的社交圈缺乏多样性。我意识到,骄傲并不是从闪耀的彩带和音乐游行开始的,而是源于抵抗——1969年的石墙骚乱,正是由像玛莎·P·约翰逊这样的有色人种跨性别女性所引发,掀起了一场运动。骄傲之前,是抗争,而非带着糖果形状的彩虹麦片和派对面具。
我和朋友保罗·威廉斯就此话题进行了交谈。他说:“作为一个在这个国家的黑人同性恋者,‘包容’往往只是一句口号,这让人感到疲惫。骄傲月可能让我感觉自己置身于一个庆祝的聚光灯下,而我并不总是能确定它包含我,或像我一样的人。我们作为一个社区,依然有许多工作要做。”
因此我想说:开始对话,利用你的特权,无论是外貌、种族、财富还是自信,去接触那些可能感到无形的人。不要继续追求那些少数人眼中的认可。我们都很孤独,互联不仅仅是善意,而是我们对社区的责任。
2017年,我的母亲去世后,我对一切都产生了退缩。但我最终参加了新奥尔良的南方奢华活动,最初我对此有些评判——街头的性行为、狂欢的表现——但随着食物的发挥,我突然换了个角度:这是欢乐,选择的家庭,在一个希望我们保持安静的世界中的反抗庆祝。我意识到,这些人是我的同伴,他们理应自由表达自己。
有关骄傲“过于性别化”或“缺乏家庭友好”的争议总是存在。但我们的性一直被用来反对我们——这使我们被逮捕、病理化,甚至被谋杀。各类的同性恋表达都是强大的,它是反抗的象征。如果这一切在街头的健身裤中尽情舞动,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2019年,我和我最好的朋友纳迪亚·埃万杰琳为骄傲活动创造了角色:同性恋角斗士Gajax和跨性别外星战士Transgalactica。我们穿着华丽的盔甲参加丹佛的骄傲,很快便凭借单纯的视觉奇观与陌生人建立了直接联系。这样的联系在纽约的世界骄傲活动中进一步加深,我们意外地走在了队伍的最前面。我们的服装成为了人们接近我们的借口,而这种打扮使我们成为了包容的创造者。
在疫情期间,我自学了动画,创造了运用我们角色制作的政治漫画。这样我便有后续的骄傲勇士——用目的呼喊进入虚空。
如今,借助团队的帮助,我经营Haus of Other,这是一个创意集体,致力于举办以社区为中心的骄傲活动。通过服装和艺术,我们提供快乐的反抗和激进的包容。我希望人们能够支持我的信息,骄傲勇士能够成为团结LGBTQA社区的工具,并与其他边缘和被压迫的社群如有色人种、移民和女性建立联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打破白人父权的窒息。
对我而言,骄傲意味着照镜子时感到平和。那种自我接受是我们必须共同建立和保护的。骄傲并不是一次活动,而是一个目标。这是一个共同的努力,以确保没有人被排除在外,特别是那些一直在我们运动核心的BIPOC、跨性别、残疾和非二元人士。
骄傲没有消失,但我们必须为之而战。我们通过选择包容,践行每一天。这是我们向先辈致以敬意的方式,尊重所有为生存而斗争的同性恋者,以便有一天我们能够为包容而战。
图片源于:denverpost